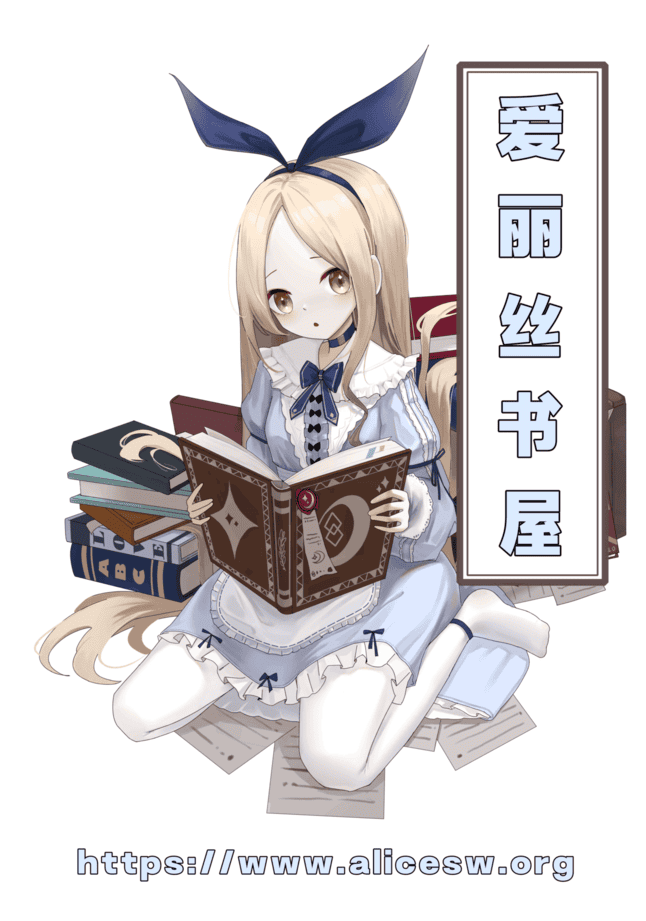“你不觉得纸偶身上浮现的是你自己的意识吗,米拉修士?”塞萨尔质问她说。
“不,他们是一些......我对往事的印象。”米拉修士说,“因为从我逐渐清醒过来之后,我就发现所有人都去世了。从那时起,往前再追溯许多年,其实我没有接手图书馆的条件和资格,无论是手腕、经验、处世、抱负都很不理想,而等我可以接手的时候,我却成了最合适的人选。我等了这么久,却除了等待一无所知,和十多岁时比起来也毫无变化,只是所有人都死了而已。至于那些无用的知识......”
“无用的知识?”
“其实很多知识对我都无意义,我只是把它们存放在我的灵魂中而已。最初的时间,它们把我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但我强迫自己整理堆积成山的书籍,按我自己的准则构筑起了这座心灵图书馆,——这就是你为什么在这里,塞萨尔。我不知道自己用了几十年还是上百年去努力回想,才搭起了最初的架构,但它往外一直延伸却未把我压垮,都是因为这些准则。”
塞萨尔忽然发现,米拉修士的回答竟然是他最初提出的问题,也即他为什么会在此处。她从他的提问里分析出了所有语义,然后,她依序把所有可能的语义都做出了解答。她回答了他想到和他没想到的每一处细枝末节,用最彻底的方式解决了他的疑问。
在这之后,这个疑问就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了。
塞萨尔意识到,这座幽深的图书馆或许就是米拉修士的心灵本身,其中的路径复杂且难寻。她想要寻求任何解释,都要从她幽深的心灵中做索引,一索引就会牵扯出一系列书籍,囊括了她能给出的一切解释。然后,她会把它们一览无余地展示出来。
“听起来戴安娜对你的活法很有兴趣。”他说,“她说她要看完这地方的所有书?”
米拉修士顿了顿,塞萨尔知道她又在自己幽深的心灵里索引了。
“比起生命的历程是否长久,”她说,“更难的,其实是让最初的想法一直伴随自己,一天接着一天,一年接着一年。其实最初的想法总会逐渐褪色,到了后来,应该把自己身上的东西称作旧习才对。我一度迷失在无穷无尽的书堆里,阅读也正是那个让我迷失其中的旧习。等我从迷失总醒来,发现自己竟然要接手一座空无一人的图书馆。我意识到自己也许无力维护那些珍惜的古籍。那里本来该由扎武隆再招一批人来修缮,但是......”
“灾难发生了?”
“这么说,你也听过那些各有政治抱负的法术团体了。”米拉修士说,“我有理由相信,其中几个影响最广泛的都有扎武隆教出的学徒参与。他们还在的时候,我把时间都用到了读书上,等我读到了写着他们的书籍,我才发现他们也已经成了历史。”
“多久远的历史?是思想瘟疫,还是土地腐朽?”
“思想瘟疫的历史太早了,那时候别说知识的黎明,知识的黑暗都还没到最深沉的时候。记得是一个年轻人拜访了我的图书馆——我记得应该是,他拿着一本书转交给我,说这是他父亲的遗书。于是我接过遗书,看到了一个人为土地腐朽的罪孽忏悔和自杀的后半生。翻阅遗书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名字,顺着字迹往下看,书上写着他还年轻的时候在图书馆里观察我的记录。”
“呃,观察你的记录?”
“我当时也在读书,我觉得应该是,我几乎没有不在读书的时候。那人写道,米拉小姐正坐在图书馆靠窗的座位上俯瞰......我倒没觉得自己在俯瞰什么东西。莱茵,他说我在俯瞰什么来着?”
“他说你在俯瞰花园,米拉大人。”纸偶莱茵说。
米拉修士颔首同意,“没错,那地方是和花园很近,不过要我自己回忆,我只记得阳光照射在书页上的气味、纹理和光晕。”
“你是说,你根本没注意到扎武隆的学徒当初在图书馆往来,你是看了本遗书才知道居然还有这个人?”塞萨尔对她发问。
“你说的对,”她说道,“我没有否认的必要。我当时把一切其它事情都抛在脑后了。我甚至没法确定那人的遗书是不是杜撰的故事。”
“因为你没有做过其它任何事,也看不到其它任何人,所以任何人杜撰故事说自己是你的同窗,你都怀疑不了?”
“虽然很不好意思,但我只记得我迷失之前认识的几个人,在那之后,我就像忽然从梦中醒来一样,发现一切都和当年不一样了。”
塞萨尔无法理解米拉修士是怎么做到这种事的,也许她根本不是人类。静默良久,他才说:“这种无法倾诉的爱意会叫人很难释怀,你想起来的时候没有感到一丝怅惘吗?”
“我不知道怅惘是什么感受,”她说,“不过,那人的遗书里确实写着一些不切实际的期望。我花了很多年记住了整座图书馆的所有书,在那之后,又急切地想要修缮所有受损的书籍,但等到腐朽扩散到图书馆的花园,我发现一切都已经无法挽回了。我本来打算和所有无法再挽救的书本们一起死去,但后来某天,有个陌生的小女孩走了过来,她看着我,很惊讶,说我居然还在被遗弃的地方等待着。”
“你觉得那个陌生的小女孩是谁,米拉修士?”
“是扎武隆,没有其它解释了。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扎武隆有很多种形象,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它都有不同的形象,老人,小孩,青年,诸如此类,共同的特征就是时间不会在它身上流逝。当时她告诉我,说船很快就会开了,如果我还想把知识延续下去,我就可以去北方表明自己的身份。”
“你很害怕扎武隆吗?我记得你当时已经很近了,再走几步就是丛林,但你还是选择绕路,避开它无限延伸的图书馆。”
“戴安娜经常和我提到你,说很多决策的深远影响会慢慢显现,这话落在扎武隆身上正合适。我起初并不明白发生了什么,后来我查清了各个法术团体的密谋者,我才发现扎武隆的学生们都怀着莫大的理想参与其中,也都扮演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与其说我害怕它,不如说,我没有信心一个人看得住它。”
“既然如此,你觉得你还不如去寻找见过它的人,比如说我们,然后和我们商议扎武隆的事情?”
“这话不假。”米拉修士说,“当年若不是我迷失在书中,也许我也会是一名身怀罪孽的法师,最终免不了会怀着巨大的罪恶感了结余生,和下沉的板块一起葬身海底。”
“我一直在担心图书馆主人和阿尔蒂尼雅说过什么。”塞萨尔说,“听你说了扎武隆的事迹,我更担心了。”
“我不完全是过来人,”她说,“我只经历了求学和求知的部分,至于扎武隆利用它的学徒犯下罪孽,这些事我只是旁观者。我个人希望,倘若皇女当真做了什么错事,你能以最执着的姿态挽回她,并尽你所能弥补那些难以弥补的一切。一旦灵魂产生了缝隙,疯狂的愿景就会从中渗入。若是看着一个人面目全非才想起来要去拯救,那就一切都晚了。”
塞萨尔摇摇头,“你自己分明什么都没经历过,说起道理来倒是一套接着一套。”
纸偶莱茵动身离开了,看起来还有事情要做,虽然说白了就是给米拉修士记忆里无穷无尽的书籍贴标签。塞萨尔看见烛台落在地上,只好自己拿起来举着。米拉修士就着烛光展开一本手稿,羊皮纸咔啦作响。
“这座图书馆记录着很多很多人的一生。”她看着羊皮纸手稿说,“我认为,我对人们的分析并不比亲身经历者更差,这么多死者的生命相互交织,也不会比一个还活着的人缺少说服力。我听戴安娜说,你认为一切都要以自己的生命经历为准,但我认为,没有分析比亲身经历更差的理由,只是你想给自己找个存在的理由罢了。”
“如果我是那个怀着无法倾诉的爱意的人,我会让爱意从迷狂式的情欲中诞生,而不是像个傻子一样站在远处看,快死了才记起来自己要写个遗书倾诉往事。”
米拉修士稍微挑起了一丝眉毛,“我听戴安娜说,你是个在情爱之事上极不守道德戒律的人,这算是一种表现吗,塞萨尔?”
“戴安娜小时候也读过很多爱情故事,难道她会觉得自己的切身经历不如对着故事里的人物做心理分析?”
“也许只是你这样的人书中从未记载,她无法先一步分析出应对之策,只好以身尝试。”米拉修士说,“等我把你的发言记录在册,装订成书,人们就会了解你的话术,思考出应对的方式。”
“你认真的,修士?”
“我可以请你本人来写引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