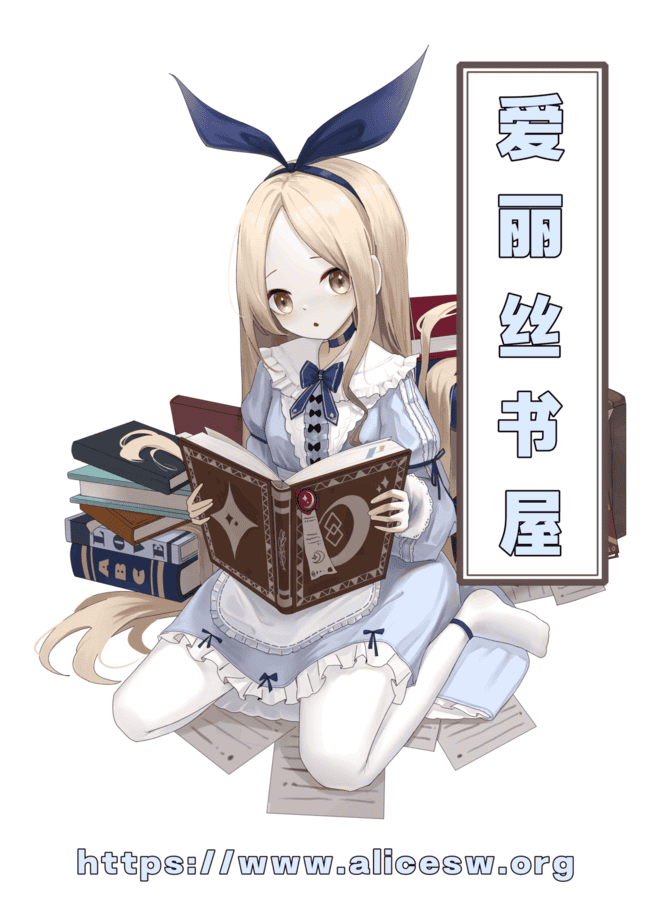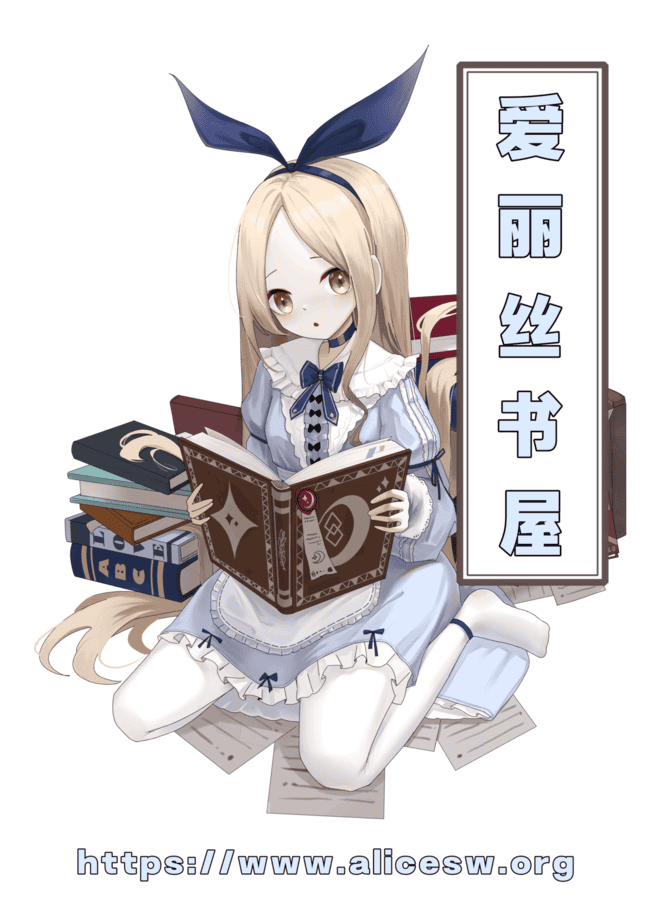穆萨里摇摇头,“她只是在个人武力冲突上更有能力。整整一座城市,以她的眼光能看出什么?”
阿婕赫往背后伸手,合拢她裂开的厚毡衣,扣好衣扣。“我是很讨厌另一个自己,但你这么说,也太贬低她的能力了。”
她的声音一如既往的凛冽,每次听她说话,穆萨里都觉得她是在站在高处训斥自己。那感觉很难描述,好像她经历的生命比他更长久,眺望的视野也比他更远似的
7
。这凭什么?就因为她能在古老精怪的梦中穿行吗?
穆萨里斜过视线,沿大帐缝隙瞥向帐篷外缓缓蠕动的双头蛇身躯。在这里看,它就像一堵巍峨的高墙。
况且他也不觉得自己在贬低,——她太把自己分裂出的另一个面目当回事了。
“我并无贬低之意,我只是从历史中得到了自己的结论。”穆萨里摇摇众筹群肆伍⑥一②⑦玖肆零头说。
“历史?说来听听。”
“就在东方的恐怖降临的那些年。”穆萨里道,“你还记得伊斯克里格的故事吗?那些年里,失魂的婴孩大多都被父母抛弃,丢入荒野,众多饥饿的野兽群聚起来,撕咬他们,却像身中剧毒一样暴毙当场。人们看到扭曲的兽尸堆积如山,久久不能腐烂,受污染的灵魂徘徊不散,逐渐填满了那些奄奄一息的血肉空壳。于是长着野兽爪牙和头颅的孽物从尸堆中诞生了,——就像她从你脊背中挣扎而出一样。”
“听起来,”阿婕赫说,“你觉得野兽人最早的起源就像从我脊背中爬出来的另一个我。”
“是你父亲这么认为。”穆萨里指出,“他说你几乎让他以为自己回到了千年以前。他们叫野兽人‘莫斯格’,意为灾难和毁灭,就像它们不是一个种族,而是一种自然现象。伊斯克里格经常和我讲述那些东西,说莫斯格是怎样怀着莫大的执着憎恨一切,描述它们是怎么屠杀人类,摧毁城市和村庄,从无止境的暴力、屠杀和虐待行为中获取力量。而且它们总是能和野兽、人类交媾,繁衍出更多自己的同胞。”
“于是?”
“当年很多人以为那些恐怖的野兽人会代替人类,成为世界的新主人,结果呢?结果北方帝国的先王从另一个大陆远渡重洋而来,一举把它们打为军事奴隶,一统治就是近千年。那些野兽人当了这么久的奴隶,直到几十年前才群聚暴动,发起了颠覆帝国的起义——就像一群无法忍受压迫的农奴一样。难道这不能让你意识到什么吗?”
“这听起来确实很有趣。”阿婕赫说,“所以你去庇护深渊以东旅行了这么久,你获得了什么更高明的看法呢?”
“我从帝国的学者那里获得了很多,阿婕赫。我阅读了很多历史文献、翻阅过很多研究资料,我甚至潜入过各个城市的图书馆,就是为了了解不同时期的文明和历史。”
“也包括野兽人的历史?”
“关于野兽人的历史,我唯一的结论就是它们没有历史。”穆萨里断言说。
这描述似乎让阿婕赫心里动了动,手指也抬了一下。
“你说他们没有历史?”她问道。
穆萨里注意到了称呼的不同,——“他们”和“它们”,但他还是点点头,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她想怎么称呼,都是她自己的事情。
“虽然很多人都把野兽人当成有智慧、通人言的类人种族,但我发现不管是哪个时代,记载它们的文献都像昨天刚刚写下的记录。从伊斯克里格讲述的年代直到现在,野兽人从来没变过,就算它们杀死了卡萨尔帝国的皇帝,发起了前所未有的暴动,它们还是和一千年多前参与灭亡了库纳人帝国的那些野兽人没区别。”
“是个挺有建树的想法。”阿婕赫同意说,“但我觉得,分裂前夕的帝国人和千年以前的帝国人也没多少区别。”
穆萨里摇摇头:“这不一样。经过许多世纪,卡萨尔帝国其实改变了很多,只是你未曾翻阅过他们不同时期的历史记载而已。野兽人却完全没有,——它们没有真正的文明,也不存在自己的历史,假装说着人言,却接受不了任何思想变化。北方的帝国为了统治自己的子民无数次加强集权,修改律法,但当年他们是怎么奴役野兽人的,如今他们也还是用一样的法子,连细节都不需要变。”
“那么暴动呢?”
“野兽人发起暴动,只是因为卡萨尔帝国本身无法维持了,仅此而已。事实上就算它们如今四处暴动,帝国各方也更在乎自己的内部斗争。因为帝国人知道,野兽人并不会像一个文明征服另一个文明那样威胁他们的统治,它们只是在屠杀、暴乱、像蝗虫一样到处肆虐。等帝国人的内部争斗完成了,他们还是能像过去一样奴役这些暂时失控的野蛮种族。”
阿婕赫斟酌了一下这些话的含义,说:
“我听明白你的看法了,穆萨里......你认为野兽人的优势只体现在个体性的狡诈和暴力行为上。一旦上升到更大层面的斗争,他们就只是群目光短浅的野兽,一群无法摆脱天性的蛮族。而且,这个看法也能套用到另一个我身上。”
穆萨里瞥向她背后的帐篷布,也许她的另一个面目就在那儿盯着他,满怀着恶意侮辱他以回应他的侮辱,但他并不在乎。
“现在你知道我没有在贬低任何人了,阿婕赫,我只是知道她擅长什么,以及她不擅
8
长什么。”他解释道。
说到这里,他们两人的发言都停下了。阿婕赫伸手拿起卷轴,端详卷轴上描绘出的人脸。她控制着呼吸,轻轻呼气。
“我不否认你的想法确实有道理。”她开口说,“只不过.......”
“只不过什么?”
阿婕赫抬眼面对他,似乎在审视他。“你眼里的战争算是什么?”
“工具。”穆萨里平静地回答,接着又补充说,“通常来说,还是最好用的工具。如果你想达成什么目的却得不到其他势力的尊重,一场战争就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那些无谓的屠杀行为不过是些附加的装饰品,有时候用得上,有时候用不上。”
阿婕赫闻言再次低下头,对着卷轴沉思了一会儿,“那么这人是谁?”
“我说过了,他是城主的私生子,也许还是唯一的儿子。你可以叫他塞萨尔,也可以叫他小博尔吉亚。”
“杀害这个塞萨尔也是工具?”
“是一个相对重要的工具,——为此法兰人会给我们提供更多援助、更多情报。就像现在我拿到了诺依恩城外制硝场的收获时间。我会派支先头部队,配合内应拿下它,并且恰当地利用它,拿法兰人的火药对付法兰人自己。”说到这里,穆萨里脸上挂起微笑,“有利条件逐渐累积,这场战事就会变得越来越顺利。我希望你也能记住这张脸,阿婕赫,每个萨苏莱人都有义务完成这件事。”
阿婕赫却偏了下头,瞥向她身后某个看不见的暗影。
她先倾听了一会儿另一个面目的发言,然后转回脸来,说:“她要我传句话,穆萨里,你只是个夸夸其谈的鸡奸者,你所谓的作战经验就是带着部族剿了几支盗匪。你把战争当成斗智甚至是弈棋,那你最终的下场就是眼睁睁看着你扔出去的棋子自行其是,把你拿着几张纸臆想出的东西都变成屠杀、暴动和失序的混乱。”
穆萨里根本懒得反驳。
结果会证明一切。
......
塞萨尔满头大汗地醒来,一边把像蜘蛛一样缠在自己身上的菲尔丝扯下来,一边踉踉跄跄奔向洗漱台。天色已经大亮了,晨练早就该开始了,他却连早饭都没吃,他甚至没吃晚饭。
他饥肠辘辘,头疼的要死,而且胃里全是辛辣的酒味。昨晚菲尔丝好奇,于是他俩连夜把加西亚留下的那瓶迷迭香花露酒祸害得一干二净,兴头上来的时候,还给狗子喂了一点。他不得不使唤狗子去弄几片面包和熏鱼过来,自己往嘴里塞几片,又给迷迷糊糊的菲尔丝嘴里塞几片,拉着狗子推门就往外跑。
等到了院子里,塞萨尔衣冠不整,还迟来了十多分钟。他本以为自己会收获一场强度不低的惩罚性训练,却只得到了来自塞希雅的冷冰冰的注视。不得不承认,她这眼神很漂亮,竟让他产生了羞愧以外的兴致。
“箱子里有适合你体型的半身甲,神殿特地给你订制的。”她说,“穿上盔甲,戴上掩饰身份的头盔,跟我还有神殿的人出去一趟。这边出了些乱子,神殿要帮忙镇压,我也有义务跟着,就当你今天的特别训练了。”
“乱子?”塞萨尔有些吃惊。能出什么乱子?
“有旅商在酒馆里吹嘘自己看到了草原人的部队。”
“在哪看到的?”
“不清楚,有人说还在刀锋山,有人说已经到了城外,还有人说草原人已经攻破了城门。我最近听说的消息是草原人骑着马从矿洞里冲出来了,正在武力占领工厂。现在城里到处都是暴民在纵火抢劫,最严重的火势已经烧了两个街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