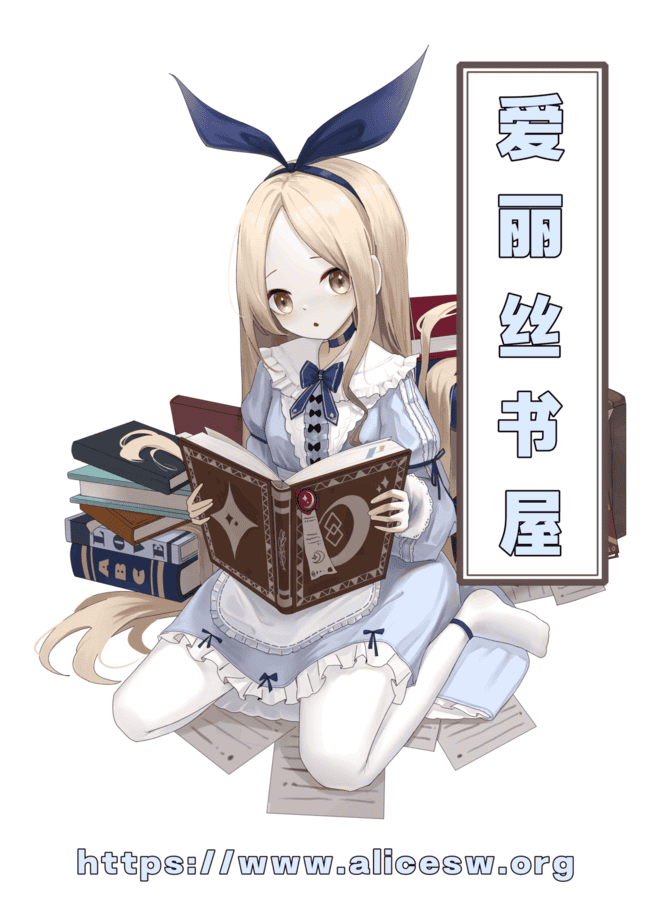“所以你打听到了那个谁都不知道真面目的人吗?”菲尔丝问他。
塞萨尔只好承认他没有:“我只知道那人算是乌比诺妻子和孩子的先祖,也许还有血缘关系。”
“我才不关心这种攀亲附会的传闻,和那个人本身没关系就别讲了。所以叶斯特伦学派怎么了?”
“好吧,事情是这样的:奥利丹的预期很简单,效仿卡萨尔帝国和奥韦拉学派,让叶斯特伦学派成为单纯为宫廷服务的法术派系。不过,法师们有不同的想法。他们的使者来了趟奥利丹,拜访了很多地方。最初奥利丹以为他们是想和贵族们拉拢关系,为以后的人脉关系做铺垫,等使者们返回学派、做完了商讨、发来了信件,奥利丹发现事情和他们想象中不一样。”
“听起来他们不想当宫廷法师?”
“叶斯特伦学派盯上了奥利丹的丹顿大学。法师们同意带着所有真知和人手迁移到奥利丹,但他们想效仿丹顿大学,而不是效仿奥韦拉学派当宫廷法师。”
“我不太理解大学是什么。”菲尔丝说。
“这个事情很复杂,不过对叶斯特伦学派,他们的诉求倒是不复杂。你知道他们的使者来奥利丹都城的时候看到了什么吗?”
“不要卖关子。”她咕哝着蜷了下身子。
“当时丹顿大学的学生和本地人集体械斗,死了不少人。最初是从各地来的贵族子弟聚在一起没事干,就开始群集酗酒,结果有人酒劲上了头,酒馆里有名的漂亮姑娘从学生们身边经过,就有人一把抱住姑娘的腰,用沾着酒的嘴唇亲了姑娘的嘴。都城酒馆里的酒友们向来看不起乡下贵族,群情激奋,和大学生们吵了起来。没过多久,人们就开始斗殴了。他们打翻了桌子、椅子、酒桶,把陶罐的碎片和葡萄酒洒得到处都是,然后还动了刀、见了血。”
“我还是没法理解这事为什么会影响叶斯特伦学派的想法。”
“因为只要愿意调查,就从这件事里查出很多东西。”塞萨尔说,接着继续讲述当时的故事,“后来斗殴升级了,理由也不复杂,都城的居民一直都看不惯丹顿大学的学生,把他们当成奥利丹全国各地闲散贵族子弟聚成的流氓团伙。那么究竟是什么影响了叶斯特伦学派的想法呢?他们调查到一件事,丹顿大学落座在郊区,和都城划出了一条界限,两边在各种意义上都互相不干涉。”
“就像两个王国一样?”
“确实很像两个王国。丹顿大学有教会的保护,还有王室特许状,财产和税收自己控制,学生和教师也有司法豁免权。那儿的人可以无视绝大多数都城的法律,只听大学自己制定的律法,所以,居民们经常能看到学生在城区闹事却没法去管。”
“从居民的视角来看真是灾难。”菲尔丝说,“那么,叶斯特伦学派是觉得,与其去当宫廷法师,享受王室的特权,不如学丹顿大学建起一个半独立的团体?”
“丹顿大学把毕业的学生送给奥利丹王国,但教授们可以一直在大学里做自己的事情,我猜叶斯特伦学派也这么想,——把只是经过培养的法师送到宫廷去,值得信任的自己人就在他们拥有的一片地界里做研究。”
“也不是不能想象。”菲尔丝同意说,“当宫廷法师特权更大,但要做的事情、要听的吩咐也更多,有时候,确实不如一个相对自由的自治团体。”
“我听说他们的初步协议已经达成了,现在正就具体的条款细节做讨价还价,如果我们过去,也许刚好能赶上。”
“我不知道,不过,正在迁移和寻求转变的学派,可能是比还待在高塔上的学派好接触。”
“看来你同意搁置去本源学会的事情了。”
“这和你拐弯抹角的话术分不开关系。”
“拐弯抹角是我的专长。”塞萨尔耸耸肩说,“而且,如果我说的太直接,我怕你会拒绝的更直接。”
菲尔丝心不在焉地掰着他的手指,一边掰,一边低声嘀咕了起来。
“谁让你当时答应得像是发了了不得的誓言一样......至少我现在知道所谓的誓言和约定都是鬼话了。”
“这说明我实际做过的事情也深得你的认同,要不然,我这几年就只能和你书信往来了。”塞萨尔辩解说。
“我觉得这和你骗人的话
11
术特别动听关系更大。”菲尔丝说道。她扔掉他的手,披着被单站到窗边,给她自己又倒了杯酒。她在月光下看起来是银白色的,头发也很细碎,就像是海岸上的冰,并非冰川,而是破碎的冰凌。塞萨尔总感觉自己无法长久地抓牢她。她会化掉,会飘走,会不注意就从他手上滑落掉。
“你在看什么?”他问。
“研究奥利丹人和多米尼人有什么区别。”她说。
“我觉得你更应该研究这个世界的人类和另一个世界的人类有什么区别。”塞萨尔说。
菲尔丝用手拉着被单,把杯子放在木桌上,小心地斟着酒。“那我不是只能研究你了?”她问道。
“有什么不好吗?”塞萨尔反问道,“珍惜的研究目标无处可寻,你却刚好得到了唯一的一份。”
“任何人在这世界上都是唯一的一份。”菲尔丝说。
“任何人在这世界上都是唯一的一份有什么不好吗?”
“唯一的一份到处都是,就说明唯一的一份是种烂大街的东西,完全不值得在乎。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一样。总之你别用那些老套的伤感故事打动我了,我的心不会流血,而且也不会流泪。”她坚持说。
“好吧,那让我们为你不会流血也不会流泪的心干一杯。”塞萨尔起身过去,完全没穿衣服,也没像她那样裹着被单。“但你为什么不会呢?”他又问道。
“可能是人如果一无所有,就不怕失去任何东西吧。”
“你当时就是抱着这种想法把密仪石扔给了我?也不管我把它随便扔到哪去?”
“有什么不对吗?”菲尔丝喝下酒杯里的酒,“你就是这个想要,那个也想要,结果就被困在了里面。这是你自己给自己造的牢笼。像我呢,我就是许多年来都一无所有,所以我什么都不怕。”
“那现在呢?”
塞萨尔拿起她的手放在自己嘴唇上,触碰了一下她纤长的指尖,这自然不是情人之间的吻,而是某种更庄重的表达。
菲尔丝咕哝了一声,不说话了。
......
“我不知道这个菲瑞尔丝在干什么。”瓶中人隔着朦胧的晨雾注视正在列队的军阵,“我不在乎他们最后会有何结局,也不在乎此事会不会是历史的重演。但她天才的行为已经冒犯了我的付出。我从失落的历史中拉她回来,不是为了欣赏这个。”
“主人?”柯瑞妮从梳妆镜前扭过脑袋,“父亲?你为什么要关注再过不久就要退场的人?”
“因为菲瑞尔丝已经证明了自己可以成就非凡之事。”瓶中人似乎在表达遗憾。“奥韦拉学派就是她的证明,”它解释说,“即使是一个分裂出去的残片,也该拥有她曾经的资质和能力,造成莫大的影响。若非我当初答应了她不做干涉,我真想......”
“你很在乎自己的承诺吗,父亲?”
“我当然很在乎,就算我不在乎,我们的协定也涉及那扇不可跨越的大门,无人能违抗......至少在时机来临前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