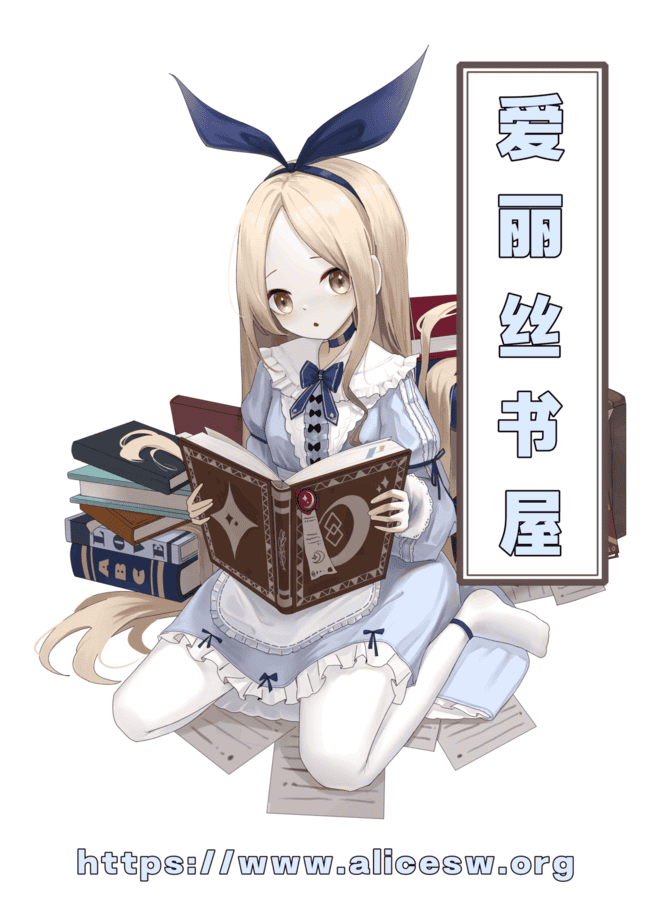“我开始头疼了。”塞萨尔说,“如果米拉瓦在残忆里发现事情不对,我是不是得考虑怎么应对他的狂怒了?”
阿婕赫抚摸着他的胸膛,锐利的爪尖挠过去带着丝丝痛楚,然后是绵软的肉垫,裹在他胸口前比人类纤细的手指还要舒服一些。她看着有些倦怠。“你都和他的皇后缠绵了这么久了,现在你来问我?”她反问他说。
“我是被迫的。”他指出。
“那个无名的男孩甚至还没和亚尔兰蒂见过面就死了,你被迫与否又有什么所谓?”
“我很怀疑米拉瓦究竟为了怀疑杀了多少人。”塞萨尔说,“亚尔兰蒂确实对那男孩产生了情愫,因此她才会记得。但在那男孩之外,又有多少人她只是看了一眼就被米拉瓦带走了?”
“你可真敢猜。”阿婕赫说。
“过度自负的人遭遇失败,很容易陷入过度的自我怀疑。你应该知道我猜的准不准吧,阿婕赫?”
“这可不好说啊?”她事不关己,“想知道米拉瓦究竟为这事杀了多少人,你就自己沿着残忆追溯去吧。”
塞萨尔在她屁股上拍了一巴掌,她立刻回咬了他胸口一口,鲜血从齿印中渗出,染在她脸颊,绒毛顿时褪去。接着她仰起那张白皙的脸颊,带着血的舌头从他嘴唇舔过,又咬在他颈侧,刻下另一圈齿印。
那条尾巴在她屁股后面摆来摆去,显得十足亢奋。他知道,这家伙一亢奋就想咬人。
他扯着她的尾巴打她裸露的屁股,不由得也躁动起来。说实话,这家伙屁股的手感异常美好,没有绒毛时滑嫩白皙,圆润无比,弹性十足,覆着绒毛时还会多出一股柔顺感。他不住拍打,令她脸颊泛红,尾巴直摇,顺着他的脖子一路咬了下去。等到最后他们用一个深吻结束了打闹,他从颈部到腰腹已经有十多道咬痕了。
塞萨尔和她互相轻咬着嘴唇,和她舌尖轻触,交换着黏连的唾液。他感觉她确实有些情迷,灰眼眸重蕴含着迷乱的情愫。许多年以前她还小的时候,她是否真的把他看成过父亲?这还真是个值得思索的问题。
虽然阿婕赫总是什么都不说,不过,只要他们沿着残忆往下追溯,或迟或早,他就能遇见阿婕赫还小的时候,能够知道这家伙如何看待菲瑞尔丝和她身侧的塞弗拉。
“说实话,”他轻轻揉捏着她的耳朵,“我在面对戴安娜的时候,我也考虑过子嗣的诞生会让无法挽回的事情发生。我也想过,如果她的感情会在这之后破碎解体,我是否应该阻止子嗣诞生?我是否该让诅咒永远都留在她的灵魂中?虽然我不会做到诅咒自己的孩子这一步,但以米拉瓦传闻中的性格......”
她颔首同意,“从后世的叶斯特伦学派来看,他们的传承不复往昔,也许不是菲瑞尔丝的过错,是米拉瓦的过错。”
“你很享受探索往事的过程?”塞萨尔问她。
阿婕赫又往他的胸口低伏下去,拿爪子在他胸口的齿痕上挠,令人发痒。“只是看你在这苦苦思索很有趣而已。”她说。
“也许米拉瓦把他们血脉传承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个古老之物——给撕裂了。有一部分生下来成了个空壳,那是她和米拉瓦的血肉之子,另一部分,它也许还困在那具缝合尸里,困在亚尔兰蒂的意识里。”
“你和她在梦和残忆中结合,它就会诞生下来。”
“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塞萨尔说。
“魂灵之子吗?”阿婕赫眨眨眼,“如果是魂灵之子,我们这边的米拉瓦和亚尔兰蒂就不止是残忆了。”
“如果我们猜的没错,那么米拉瓦不仅是困住了吉拉洛,他还撕裂了那个古老之物。虽然不知道他是怎么办到的,是只靠他自己,还是祈求了索莱尔的支持,但叶斯特伦学派在后世的传承确实出了大问题。”
“只要沿着残忆继续追溯就能找到谜底了吧。”阿婕赫语气慵懒地说,“不过,你以后可能得在残忆里扮一阵亚尔兰蒂身边的骑士和仆人了。法兰帝国皇后的情人啊.....真有意思,在现实的历史里,她生下了米拉瓦的孩子,但在残忆里,那也许会是你的孩子。”
“说实话,这事来得太莫名其妙了。”
“我这边就不莫名其妙了?”阿婕赫低头看向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眼睛微眯,“要我说,这事和我有关也和我无关,等它出来了......”
“你话里的杀意太重了。”塞萨尔打断她的发言。
阿婕赫若无其事耸耸肩,翻了个身躺在他身上。她弓起身子,伸了个十足的懒腰。她染血的纤长食指在她头顶交错,随后把两只手都抚在他脸颊上。“你这么盯着我,是又想跟我讲你的火炉小故事了吗?”她眼含戏谑的轻笑。
塞萨尔抚摸着她微微隆起的小腹,低头和她接吻。“我可以等孩子生下来再来跟你讲我的火炉小故事。”他说,“不管怎样,我至少要看看它是什么。”
阿婕赫捧着他的脸,柔唇贴着他的嘴唇轻声呵气,“说实话,我从没在乎过这事,反而是你像个怀了孩子的女人一样瞻前顾后。”
“这是爱意的表达。”塞萨尔对她说,又和她吻在一起。
“对我来说,痛楚和死亡都是爱意的表达。”她看起来并不在意,语气也很随意,“我的做法和你们人类的做法不一样。”
塞萨尔笑了,“你如果真这么做,我就像当年的塞弗拉一样用铁链把你拴起来,亲爱的。我会把项圈连着铁链套在你脖子上,把铁链的那头捆在我手上。如果这还不够,我就把你的手腕也用铁链捆起来。”
阿婕赫瞪大一双眼睛,和他对视许久。塞萨尔微笑着抚摸她的脸颊。“这一定会让事情变得非常有趣,亲爱的。”他柔声说,“在这之前,你可以好好伤害伤害我,试试你要做到哪一步才能让这件事发生。那一定会很美妙,真的,它会表达我对你的爱意究竟有多深切。”
......
不出意外,还是当年的梦境,不过,这次塞萨尔清醒了一些。他醒来时以为自己会睡在菲瑞尔丝卧室旁的侧室里,但他其实睡在亚尔兰蒂宽阔的卧榻上,床头的柜子上堆满了空荡荡的药剂瓶。
他想起来了,昨夜亚尔兰蒂看他快要昏死过去,给他连着灌了一柜子的药。直到现在他还意识迷乱,昏昏沉沉,朦胧中竟然都分不清梦和现实,觉得眼前女主人昏暗的卧室、天蓝色的绣银丝绸幔帐、摇摇晃晃的珍珠白吊灯都是一场白日梦。
塞萨尔坐起身来,掀开蓬松的被子,发现被褥竟然镶嵌着珍珠,用银丝镂着法术符文,顿时感觉这东西像是神殿的法衣,说不定就是法兰帝国那边送来的订婚礼物。所以,这家伙都当了皇帝的未婚妻还要拿仆人消遣?他感觉身子很虚弱,他知道这个年纪的男孩不应该频繁做这种事,但女主人的要求他根本没法违抗,更别说她还是个可怕的法师了。
若说菲瑞尔丝只是个阴沉的女孩,看着性格偏执,其实对她的姐姐和女仆都依赖性十足,亚尔兰蒂就是刻板印象的傲慢贵族。分明才十多岁,她的性子里就带着一股天真的邪恶和残忍。这件事情,塞萨尔已经体会的足够深刻了。
这会儿亚尔兰蒂倚靠在床头翻书,长发如飘雪铺满被褥,看起来美得惊人,不像是真的。透过窗户塞萨尔看到大雪纷纷,飘落在院中,想说点什么却舌头发涩。因为昨晚他舔了她好久,光是她的脚趾就挨个舔了一遍,后来还被她边看书边用两只灵巧的小脚戏弄,其中毫无情意可言,只是一种年少的小主人对同样年少的仆人的消遣。
现在看到他从昏迷中醒来,亚尔兰蒂用手支着下颌望了过来,她的视线饶有兴味。“昨晚菲瑞尔丝找到我,说她的塞弗拉看着不太清醒,问我发生了什么事。但我分明给她留了一部分人格,你觉得这是为什么?”她说着点在他嘴唇上,念诵了一句咒语,这才让他有了说话的力气。
“我猜我和她是完整的一部分。”塞萨尔喘了口气说,“不管是谁少了彼此都会感到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