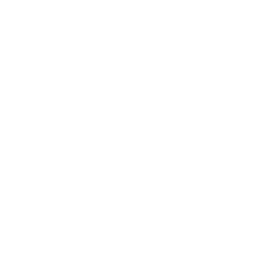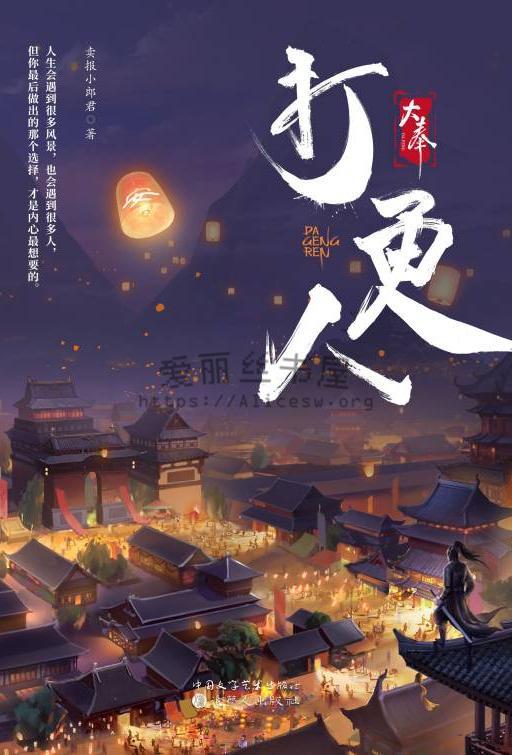第八章 日常的麻木
周洁搬来北京后的日子,表面上看似一切步入了正轨。她在新租的小公寓里安顿下来,每天早出晚归地去教育机构上班,而我则继续在实验室里忙碌,埋头于实验数据和论文撰写。
我们像一对普通的情侣,偶尔一起吃晚饭,周末去超市买点东西,甚至会在晚上挤在她的小沙发上看电影。她不再提起过去,我也刻意不去触碰那些阴影。
我开始让自己相信,只要不去想那些不堪的回忆,我们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我强迫自己专注于眼前,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验的每一步、论文的每一句话,甚至是实验室里咖啡机的嗡嗡声。
那些曾经让我痛苦不堪的画面——她在别人身下的呻吟、她被欲望支配的模样——像是被我锁进了一个深不见底的盒子,扔进了记忆的角落。
周一到周五,我按时起床,坐地铁去学校,泡在实验室里直到深夜。回到宿舍时,往往已经筋疲力尽,倒头就睡,连做梦的力气都没有。周末,周洁会来找我,或者我去她那儿。
她会做一桌子菜,笑着让我多吃点,说我太瘦了。我也会配合地吃下去,夸她手艺好,然后我们一起洗碗,聊些无关紧要的事——天气、电影、新开的餐厅。
这样的日子平淡得像白开水,却也让我感到一种奇怪的安全感。
“葛斐,你周末有空吗?我想去郊外走走。”某个周五的晚上,她窝在我怀里看完一部电影后,突然抬头问我。
我低头看着她,她的眼神清澈,带着一丝期待。我点点头:“有空,去哪儿都行。”她笑了,踮起脚亲了我的脸一下:“那就去香山吧,听说那儿的枫叶红了。”
周六早上,我们坐公交去了香山。天气很好,阳光透过车窗洒进来,照在她脸上,让她看起来温柔而明媚。
到了山脚,她拉着我往上走,一路上指着路边的树说:“你看,这棵多红,像不像火?”我随口应着:“是挺好看。”她笑得更开心了,拉着我的手跑了几步,像个孩子。
爬到半山腰时,我们找了个休息点坐下。她从背包里拿出水壶递给我:“渴了吧?喝点。”我接过来喝了一口,凉凉的,带着一点柠檬的清香。
她靠在我肩上,看着远处的山景,低声说:“葛斐,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的。你呢?”我顿了一下,低声说:“嗯,我也觉得挺好。”
这话不完全是敷衍。我确实开始习惯这种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怀疑,只有日复一日的平静。
我不再去翻她的手机,也不去猜测她下班后有没有去别的地方。我告诉自己,只要她在我身边,只要我们还能这样相处,那些过去就不重要了。
回到家后,她的工作似乎越来越忙,偶尔会加班到很晚。我也没多问,只是默默等着她发消息告诉我安全到家。
有一次,她加班到十点多才回来,打电话给我时声音有点疲惫:“葛斐,我刚到家,今天累死了。”我嗯了一声,说:“那早点休息,别太拼了。”她笑了一下:“知道啦,你也早点睡。”
挂了电话,我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她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可我却没有像以前那样急着去想象她在做什么。
我只是觉得累,累到不想再去探究什么。也许这就是正常生活的代价——麻木地接受一切,不再追究真相。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四月中旬。北京的春天来得晚,街边的柳树才刚抽出嫩芽。
我的博士研究进入关键阶段,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周洁也忙着适应新工作,我们见面的时间变少,但她依然会抽空给我发消息,提醒我吃饭、休息。
我也会回几句,简单却足够维持联系。
一个周五的下午,我刚做完一组实验,正准备收拾东西回宿舍,手机震了一下。
是周洁发来的消息:“葛斐,我今晚有个同事聚会,可能晚点回来,你别等我了。”我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回了个“好”。
她很快又发来一条:“你别生气啊,我尽量早点回来。”我没再回,只是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手头的工作。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宿舍吃了泡面,然后打开电脑写论文。窗外的夜色渐渐深了,实验室楼下的路灯亮起,投下一片昏黄的光。
我偶尔抬头看一眼时间,十点,十一点,十二点,她还是没消息。我没有给她打电话,也没有发消息催她。我只是继续敲着键盘,像个机器一样运转。
凌晨一点,手机终于响了。她发来一条语音:“葛斐,我刚到家,聚会拖得有点晚,睡了吧?”她的声音有点沙哑,像是喝了酒。我没回,关掉手机,倒头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看到她又发了一条消息:“早安,葛斐,今天我休息,要不要一起吃午饭?”我回了句:“好,中午见。”然后起床洗漱,像往常一样开始新的一天。
中午,我们在学校附近的一家小餐馆见面。她穿着一件浅绿色毛衣,头发披下来,看起来精神不错。
她笑着走过来,坐下后给我点了一份我爱吃的牛肉面:“葛斐,你昨天没生气吧?我同事非拉着我多喝了两杯。”
我摇摇头:“没生气,忙你的就好。”她松了口气,笑眯眯地说:“那就好,我还以为你会不高兴呢。”
吃饭时,她聊了些聚会上的趣事,说哪个同事喝多了出洋相,哪个领导讲了个冷笑话。我听着,时不时点点头,偶尔搭一句。
饭后,她提议去附近公园走走,我没反对,跟着她去了。
公园里人不多,春风吹过,柳枝轻轻摇晃。她拉着我的手,指着湖边的鸭子说:“你看,它们多可爱。”
我嗯了一声,低头看着湖面,心里却一片空白。我不再去想她昨晚是不是真的只是聚会,也不再去猜她身上有没有别人的痕迹。我只是跟着她走,机械地回应着她的话。
那天晚上,我留在了她公寓。她做了晚饭,我们一起看了一部老电影。电影放到一半,她靠在我怀里睡着了。
我低头看着她,她的呼吸均匀,嘴角微微上扬,像是在做一个好梦。我伸手关掉电视,把她抱到床上,自己睡在沙发上。
夜深了,我躺在沙发上,听着窗外的风声,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我不再想起那些不好的回忆,不再让自己被过去拖进深渊。
我该上班上班,该吃饭吃饭,和她相处时就好好相处。生活就像一条平坦的路,我只需要往前走,不回头,不多想。
也许这就是我能做到的最好状态——不去爱得太深,也不恨得太切,只是麻木地活着,和她一起,维持着这场虚假的正常生活。
日子在这种麻木的平静中继续流淌,我和周洁的关系像是被一层薄纱包裹,既亲近又疏离。她似乎察觉到了我内心的冷漠,却从不明说,只是用更多的温柔和关怀试图填补那道无形的裂缝。
而我,虽然不再主动回忆那些不堪的过往,却也无法完全释怀,心底的伤口始终在隐隐作痛,像一颗埋藏的种子,随时可能破土而出。
四月底的一个周末,周洁突然提议:“葛斐,我们去报个情侣疗愈课程吧?我听说那种课能帮人修复感情。”她坐在我对面,手里捧着一杯热茶,眼神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期待。
我愣了一下,随即皱眉:“疗愈课程?什么意思?”她放下杯子,认真地说:“就是那种心理辅导课,专门给情侣设计的,可以让我们更了解彼此,解决一些……潜在的问题。”
我看着她,心里一阵复杂。她口中的“潜在问题”显然是指我们之间那些未曾言明的阴影——她的背叛,我的沉默,还有我们小心翼翼维持的假象。我本想拒绝,可看到她眼里的恳求,我最终还是点了头:“好吧,试试看。”
课程定在下周六,地点是市中心一家心理咨询机构。周洁提前在网上报了名,还特意打印了课程简介给我看。
简介上写着:“通过沟通练习、情感重建和信任训练,帮助情侣找回爱的初心。”我扫了一眼,没说话,心里却有些抵触——信任还能重建吗?那些画面已经刻在我脑海里,怎么可能抹去?
到了那天,我们准时到了咨询机构。教室里已经坐了五六对情侣,有的是年轻小夫妻,有的是像我们这样的恋人。
老师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着眼镜,笑容温和。她先让我们自我介绍,我和周洁简单说了名字和交往时间,她还加了一句:“我们想让感情更稳定。”老师点点头,示意我们坐下。
课程开始后,老师先讲了一些情感修复的基本理论,比如“伤害后的信任重建需要时间和双方的坦诚”,“沟通是桥梁,沉默是障碍”。
我听着,时不时瞥一眼周洁,她坐在我旁边,低头记着笔记,像个认真听课的学生。接着,老师安排了第一个活动——“情感坦白”。
规则是每对情侣面对面坐好,轮流说出一件困扰自己的事,必须诚实,不能敷衍。轮到我们时,周洁先开口。
她看着我,犹豫了一下,低声说:“葛斐,我知道我以前做过对不起你的事,我一直很愧疚,怕你心里有疙瘩。”她的声音有点颤抖,眼圈微微发红。
我盯着她,心里像被什么堵住,酸涩得厉害。
轮到我时,我沉默了好几秒。老师鼓励道:“没关系,说出你真实的感受就好。”
我深吸一口气,终于开口:“我有时候会觉得,我们之间有东西回不去了。”我没提具体的事,但她显然听懂了,低头咬着唇,眼泪掉了下来。她伸手想拉我,被我下意识躲开了。
教室里安静得有些尴尬,老师轻声说:“没关系,慢慢来。”
接下来的活动是“信任练习”。老师让我们两人一组,一个蒙眼,一个引导,蒙眼的人要完全信任引导者,在房间里走一圈不撞到东西。
周洁自告奋勇蒙眼,我站在她身后,低声说:“往前走。”她点点头,小心翼翼迈出一步,我扶着她的肩膀,告诉她左转、右转。
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在试探,可最终还是顺利走完了全程。
摘下眼罩后,她笑着看我:“葛斐,我真的很相信你。”我勉强扯了扯嘴角,没说话。
老师在一旁说:“信任是双向的,引导者也在学习如何被依赖。”我心里冷笑:她相信我,可我还能相信她吗?
课程结束后,老师布置了作业——每天花十分钟面对面聊天,不聊琐事,只聊内心感受。我们离开时,周洁拉着我的手,说:“葛斐,我觉得今天挺有意义的,你呢?”我嗯了一声:“还行吧。”她笑了一下,没再追问。
从那天起,我们开始试着完成作业。第一天晚上,她盘腿坐在沙发上,看着我说:“我今天想到你的时候,觉得很温暖,但又有点害怕,怕你哪天会突然离开。”
她的语气很轻,像在自言自语。我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有时候会觉得累,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她愣了一下,眼泪又掉下来,可这次她没伸手拉我,只是低声说:“我明白,我会努力的。”
第二天,她说:“我很想让你开心,可我知道我以前的错让你很难开心起来。”我说:“我也在试着放下,但有些东西放不下来。”
第三天,她说:“我爱你,葛斐,比你想的要多。”我说:“我知道,可我不知道怎么再去爱得像以前那样。”
这样的对话持续了一周,每晚十分钟,像是在小心翼翼地剥开伤口,又试图涂上药膏。
她的坦白让我看到她的努力,可我的回应却总是冷淡。我不想伤害她,可我也没办法假装一切如初。
那些回忆虽然不再主动浮现,却像影子一样跟在我身后,我一转身就能看见。
课程结束后的一个月,我们的关系似乎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她变得更敏感,经常观察我的表情,问我是不是不高兴;而我则更沉默,不愿多说,怕一开口就暴露心里的挣扎。
有一天晚上,她突然抱着我哭了:“葛斐,我知道你还没原谅我,可我真的不想失去你。”我拍着她的背,低声说:“我也没说要走。”
这话像是个承诺,可我自己都不知道能兑现多久。情感修复的过程比我想象的艰难,它不是简单的道歉和原谅,而是要面对那些血淋淋的真相,再试着缝合伤口。
可我发现,我的针线不够锋利,她的伤药也不够有效。
五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我们又去了一次香山。这次不是看枫叶,而是看新发的绿芽。
她拉着我走在山路上,笑着说:“葛斐,你看这树,多新鲜,像不像我们的感情?”我看着她,挤出一个笑:“像。”
她高兴地抱住我,我回抱了一下,心里却清楚,这“新鲜”只是表面的,根底下早已腐烂。